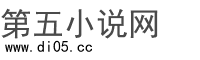(15)飞鸟之影,未尝动也(《列子》亦有“影不移”一条)。
(16)镞矢之疾,而有不行不止之时。
(17)狗非犬(《列子》有“白马非马”。与此同意。说详下)。
(18)黄马,骊牛,三。
(19)白狗黑。
(20)孤驹未尝有母(《列子》作“孤犊未尝有母”)。
(21)一尺之棰,日取其半,万世不竭(《列子》作“物不尽”)。
此外《列子》尚有“意不心”“发引千钧”两条。
四、总论
这些学说,前人往往用“诡辩”两字一笔抹杀。近人如章太炎极推崇惠施,却不重这二十一事,太炎说:
辩者之言独有“飞鸟”“镞矢”“尺棰”之辩,察明当人意。“目不见”“指不至”“轮不蹍地”亦几矣。其他多失伦。夫辩说者,务以求真,不以乱俗也。故曰“狗无色”可,云“白狗黑”则不可。名者所以召实,非以名为实也。故曰“析狗至于极微则无狗”可,云“狗非犬”则不可。(《明见》篇)
太炎此说似乎有点冤枉这些辩者了。我且把这二十一事分为四组(第八条未详,故不列入),每组论一个大问题。
第一,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。(3)(9)(15)(16)(21)
第二,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。这一组又分两层:
(甲)从“自相”上看来,万物毕异。(13)(14)(17)
(乙)从“共相”上看来,万物毕同。(1)(5)(6)(12)
第三,论知识。(2)(7)(10)(11)(18)
第四,论名。(4)(19)(20)
五、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
惠施也曾有此说,但公孙龙一般人的说法更为奥妙。(21)条说“一尺之棰,日取其半,万世不竭”。这一条可引《墨子·经下》来参证。《经下》说:
非半弗则不动,说在端。《经说》曰:半,进前取也。前则中无为半,犹端也。前后取,则端中也。必半,毋与非半,不可也。
这都是说中分一线,又中分剩下的一半,又中分一半的一半,……如此做法,终不能分完。分到“中无为半”的时候,还有一“点”在,故说“前则中无为半,犹端也”。若前后可取,则是“点”在中间,还可分析,故说“前后取,则端中也”。司马彪注《天下》篇云:“若其可析,则常有两;若其不可析,其一常在。”与《经说下》所说正合。《列子·仲尼》篇直说是“物不尽”。魏牟解说道:“尽物者常有。”这是说,若要割断一物(例如一线),先须经过这线的一半,又须过一半的一半,以此递进,虽到极小的一点,终有余剩,不到绝对的零点。因此可见一切空间的分割区别,都非实有,实有的空间是无穷无尽,不可分析的。
(16)条说:“镞矢之疾,而有不行不止之时。”说飞箭“不止”,是容易懂得的。如何可说他“不行”呢?今假定箭射过百步需三秒钟。可见他每过一点,需时三秒之几分之几。既然每过一点必需时若干,可见他每过一点必停止若干时。司马彪说:“形分止,势分行。形分明者行迟,势分明者行速。”从箭的“势”看去,箭是“不止”的。从“形”看去,箭是“不行”的。譬如我们看电影戏,见人马飞动,其实只是一张一张不动的影片,看影戏时只见“势”不见“形”,故觉得人马飞动,男女跳舞。影戏完了,再看那取下的影片,只见“形”,不见“势”,始知全都是节节分断,不连络,不活动的片段。
(15)条说:“飞鸟之影,未尝动也。”《列子·仲尼》篇作“影不移”。魏牟解说道:“影不移,说在改也。”《经下》也说:
景不从,说在改为。《经说》曰:景,光至景亡。若在,万古息。
这是说,影处处改换,后影已非前影。前影虽看不见,其实只在原处。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地照下来,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。
(9)条“轮不蹍地”,与上两条同意,不过(9)条是从反面着想。从“势”一方面看来,车轮转时,并不蹍地;鸟飞时,只成一影;箭行时,并不停止。从“形”一方面看来,车轮转处,处处蹍地;鸟飞时,鸟也处处停止,影也处处停止;箭行时,只不曾动。
(3)条“郢有天下”,即是庄子所说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,而太山为小”之意。郢虽小,天下虽大,比起那无穷无极的空间来,两者都无甚分别,故可说“郢有天下”。
这几条所说只要证明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是主观的区别,并非实有。
六、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
(甲)从自相上看来,万物毕异。
《经下》说:“一法者之相与也,尽类,若方之相合也。”这是从“共相”上着想,故可说同法的必定相类,方与方相类,圆与圆相类。但是若从“自相”上着想,一个模子铸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钱;一副规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圆;一个矩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方。故(13)条说:“矩不方,规不可以为圆。”(14)条“凿不围枘”,也是此理。我们平常说矩可为方,规可为圆,凿恰围枘:这都不过是为实际上的便利,姑且假定如此,其实是不如此的。(17)条“狗非犬”,也是这个道理。《尔雅》说:“犬未成豪曰狗。”《经下》说:
狗,犬也。而“杀狗非杀犬也”可。
《小取》篇说:
盗人,人也。多盗,非多人也。无盗,非无人也。……爱盗,非爱人也。杀盗,非杀人也。
这几条说的只是一个道理。从“共相”上着想,狗是犬的一部,盗是人的一部,故可说:“狗,犬也。”“盗人,人也。”但是若从“自相”的区别看来,“未成豪”的犬(邵晋涵云:“犬子生而长毛未成者为狗”),始可叫作“狗”(《曲礼》疏云:通而言之,狗、犬通名。若分而言之,则大者为犬,小者为狗)。偷东西的人,始可叫作“盗”。故可说:“杀狗非杀犬也”“杀盗非杀人也”。
公孙龙的“白马非马”说,也是这个道理。《公孙龙子·白马》篇说:
“马”者,所以命形也。“白”者,所以命色也。……求“马”,黄黑马皆可致。求“白马”,黄黑马不可致。……黄黑马一也,而可以应“有马”,不可以应“有白马”。是白马之非马,审矣。……“马”者,无取于色,故黄黑马皆可以应。“白马”者,有去取于色,黄黑马皆以所色去,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。
这一段说单从物体“自相”的区别上着想,便和泛指那物体的“类名”不同。这种议论,本极容易懂,今更用图表示上文所说:
(乙)从共相上看来,万物毕同。
(1)条说:“卵有毛。”这条含有一个生物学的重要问题。当时很有人研究生物学,有一派生物进化论说:
万物皆种也,以不同形相禅(《庄子·寓言》)。
种有几(几即是极微细的种子。几字从,字从,本像胚胎之形)。……万物皆出于几(今作机,误。下几字同),皆入于几(《庄子·至乐》)。
这学说的大意是说生物进化都起于一种极微细的种子,后来渐渐进化,“以不同形相禅”,从极下等的微生物,一步一步地进到最高等的人(说详《庄子·至乐》篇及《列子·天瑞》篇)。因为生物如此进化,可见那些种子里面,都含有万物的“可能性”(亦名潜性),所以能渐渐地由这种“可能性”变为种种物类的“现形性”(亦名显性)。又可见生物进化的前一级,便含有后一级的“可能性”。故可说:“卵有毛。”例如鸡卵中已含有鸡形;若卵无毛,何以能变成有毛的鸡呢?反过来说,如(5)条的“马有卵”,马虽不是“卵生”的,却未必不曾经过“卵生”的一种阶级。又如(6)条的“丁子有尾”。成玄英说楚人叫虾蟆作丁子。虾蟆虽无尾,却曾经有尾的。第(12)条“龟长于蛇”,似乎也指龟有“长于蛇”的“可能性”。
以上(甲)(乙)两组,一说从自性上看去,万物毕异;一说从根本的共性上看去,从生物进化的阶级上看去,万物又可说毕同。观点注重自性,则“狗非犬”“白马非马”;观点注重共性,则“卵有毛”“马有卵”。于此可见,一切同异的区别都不是绝对的。
七、论知识
以上所说,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,论万物毕同毕异,与惠施大旨相同。但公孙龙一班人从这些理论上,便造出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。他们以为这种区别同异,都由于心神的作用,所以(7)条说“火不热”,(10)条说“目不见”。若没有能知觉的心神,虽有火也不觉热,虽有眼也不能见物了。(2)条说“鸡有三足”。司马彪说鸡的两脚需“神”方才可动,故说“三足”。公孙龙又说“臧三耳”,依司马彪说,臧的第三只耳朵也必是他的心神了。《经上》篇说:“闻,耳之聪也。循所闻而意得见,心之察也。”正是此意。
《公孙龙子》的《坚白论》,也可与上文所说三条互相印证。《坚白论》的大旨是说,若没有心官做一个知觉的总机关,则一切感觉都是散漫不相统属的;但可有这种感觉和那种感觉,决不能有连络贯串的知识。所以说“坚白石二”。若没有心官的作用,我们但可有一种“坚”的感觉和一种“白”的感觉,决不能有“一个坚白石”的知识。所以说:
无坚得白,其举也二。无白得坚,其举也二。
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,无坚也。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,无白也。……得其白,得其坚,见与不见离。(见)不见离,一二不相盈,故离。离也者,藏也。(见不见离一, 二不相盈故离。旧本有脱误。今据《墨子·经说下》考正)
古来解这段的人都把“离”字说错了。本书明说:“离也者,藏也。”离字本有“连属”的意思,如《易·彖传》说:“离,丽也。日月丽乎天,百谷草木丽乎土。”又如《礼记》说:“离坐离立,毋往参焉。”眼但见白,而不见坚,手可得坚,而不见白。所见与所不见相藏相附丽,始成的“一”个坚白石。这都是心神的作用,始能使人同时“得其坚,得其白”。
(18)条“黄马骊牛三”,与“坚白石二”同意。若没有心神的作用,我们但有一种“黄”的感觉,一种“骊”的感觉和一种高大兽形的感觉,却不能有“一匹黄马”和“一只骊牛”的感觉,故可说“黄马骊牛三”。
最难解的是(11)条“指不至,至不绝”。我们先须考定“指”字的意义。《公孙龙子》的《指物》篇用了许多“指”字,仔细看来,似乎“指”字都是说物体的种种表德,如形色等等。《指物》说:
物莫非指,而指非指天下无指,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,天下无物,可谓指乎?(无物之无,旧作而。今依俞樾校改)
我们所以能知物,全靠形色、大小等等“物指”。譬如白马,除了白色和马形,便无“白马”可知,故说“物莫非指”,又说“天下无指,物无可以谓物”,这几乎成了极端的唯心论了。故又转一句说“而指非指”,又说“天下无物,可谓指乎?”这些“指”究竟是物的指。没有指固不可谓物,但是若没有“物”,也就没有“指”了。有这一转,方才免了极端的唯心论。
(11)条的“指”字也作物的表德解。我们知物,只须知物的形色等等表德。并不到物的本体,也并不用到物的本体。即使要想知物的本体,也是枉然,至多不过从这一层物指进到那一层物指罢了。例如我们知水,只是知水的性质。化学家更进一层,说水是氢氧二气做的,其实还只是知道氢气、氧气的重量作用等等物指。即使更进一层,到了氢气、氧气的元子或电子,还只是知道元子、电子的性质作用,终竟不知元子、电子的本体。这就是(11)条的“指不至,至不绝”。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,再也不会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