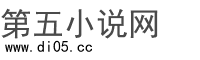殷知行的话同样问住了帝君殷昭。
的确,按道理来说,若是宁尘真要投靠盛乾王朝,那大半个月过去了,怎么也不该还在天元王朝的西北之地待着。
“父皇。”
“儿臣再问。”
“若是宁尘真的想隐瞒行踪,若是真的毫无悲悯之心,那他会只是伤了几个村民,杀了几个修行者吗?”
“他又不是傻子,难道不该把所有人都斩草除根,确保自己的行踪不会暴露?”
殷知行又问道。
尽管阴差阳错之下,招来父亲的误解。
但他还是竭力凭借眼下所掌握的线索,还原着真相。
一位隶属于太子殷砚辞派系的大臣冷笑一声:
“呵呵,所以三皇子殿下的意思是,这宁尘是出于无奈。”
“离开萧家是无奈,杀了萧家族人是无奈,一路躲藏是无奈,伤及无辜村民、修行者还是无奈……”
“老臣倒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身上哪来的那么多无奈?”
“若是真的在萧家受了天大的委屈,直接请朝廷出面为他作主不就行了?”
“他可是当年国战的头号功臣,不找朝廷到底是心里有鬼,还是连朝廷都信不过了呢?”
对方所抛出的两种可能,都对宁尘分外不利。
且仍旧是紧抓住现在说不通的关键命门,想叫殷知行哑口无言。
然而殷知行这十几日来,却是并非虚度光阴。
再次面对这一问题,他没有语塞,而是朗声道:
“是谁说的宁尘没打算请朝廷出面?”
“他刚离开萧家,就写了书信同我说明情况,这不足以说明他没有想过隐瞒吗?”
“可谁给过他机会?”
“刚刚离开萧家,萧家就派人追杀他。还没等几日,连朝廷都下发了通缉告示,给他头上扣上了叛国的罪名!”
“没有人给他机会,不等他辩解,就已经逼着他往绝路上走!”
那大臣又是嗤笑了一声:
“三皇子殿下可不要本末倒置了。”
“分明是他没有第一时间解释,朝廷才不得不放出通缉告示。”
“但凡他出面,您觉得陛下会有意偏袒萧家,冷落国战功臣?”
殷知行冷视对方,驳斥道:
“书信在此,这还不叫第一时间解释?”
“那你来说说,到底多快才叫第一时间?”
那大臣耸耸肩,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:
“三皇子殿下。”
“这书信是真是假,我们都尚且难以确认。”
“您非要拿这么一件还不具备什么价值的物证说事,怕是难以服众呀。”
太子一派的人,将矛头再次对准了书信。
只要能一口咬死书信是殷知行伪造的,那么殷知行为宁尘开脱的话,就都丧失了可信度。
不止如此。
明晃晃地欺瞒帝君,其先前辛苦数年积累出的形象,也将轰然崩塌。
到时帝君势必会对其怀有戒心,放弃重用,把精力重新放在培养太子身上。
可以说,殷知行越为宁尘出头,就越会陷入泥沼。
这一点,殷知行自己也再清楚不过,可他从未有过任何的犹豫与顾虑:
“书信就在这里,信使也还在皇宫之内,随时可以召见。”
“这一路走来,也自然会有数不尽的痕迹留下。”
“我殷知行堂堂正正,不怕被查。”
“若是谁信不过,大可前去调查一番,拿出证据。”
“都是朝廷重臣,理应知道谁主张谁举证的道理。否则随便一句质疑,就叫别人的努力付之一炬,这才是真正的难以服众!”
殷知行足够的光明磊落。
他所崭露出的气场与坦诚,也叫坐在帝位之上的帝君殷昭不免动摇。
这孩子做事向来稳妥。
当年国战,天元王朝一退再退,军心涣散,迫切需要皇室出面稳固军心。
作为一国之君,殷昭不能随便离开。而太子殷砚辞又突然宣称染上疾病,无力出面。那时只有殷知行主动站了出来,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,为天元王朝贡献绵薄之力。
这么一个把国家利益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人,也不太可能为了一个叛国之贼,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。